諾獎獲得者:核電研究不能停
2012/04/0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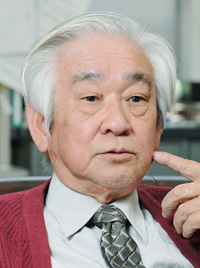 |
| 益川敏英 |
記者:科學可以為日本震後的復興做些什麼?
益川敏英:科學家平時做研究的過程中思考眼前的課題會更有意思。因為如果只沉醉於在研究競爭中獲勝就不會關注社會現實。科學和文化具有相同的地方,那就是二者都不會立刻見效。如果你要問對災民有沒有用處,只能説不能馬上派上用場,一般大約要到30年後才會有結果。
記者:而社會越來越需要那些有用的研究。
益川敏英:不僅是科學,一切學問都是為了豐富人類社會和生活。以河流為例,從上游流過來養分,下游的花朵因此才能盛開。科學也一樣,一旦上游枯竭科學自身很快也會衰敗。」
以政治為例,我認為與「精英政治」相比「草民政治」的形式更好一些。所謂精英政治,就是由優秀的人決定方向、做出指示,然後會出現好的結果,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。一旦方向指錯了,為提高效率而做的各種事情都會適得其反,甚至會全搞砸。與其那樣倒不如讓大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肯定會有人找到正確的答案。
記者:也有人認為,科學應該和政治、社會走得更近一些。
益川敏英:科學家不深入到社會活動之中就不能真正地思考和平與未來的問題。如果不考慮子孫以後會怎麼樣、這樣下去行嗎等等問題,則科學發展就沒有動力。不過歷史上科學家也曾被政治利用過。例如,一個科學家小組早於德國率先在美國進行原子彈開發並獲得成功,還指出將來核武器應該由國際管理,但美國一掌握核武器就不再放手了。問題一旦帶上政治色彩,就不再是科學家力所能及的了。
記者:您怎麼看待福島第1核電站事故?
益川敏英:與普通災害和事故不同,核電事故有輻射污染問題,所以其危害可能像原蘇聯車諾比爾事故那樣會持續20~30年,而日本並沒有充分考慮好如何應對這種情況。使問題複雜化的是對安全性的認識。核電站選址時,沒有當地居民同意就不能建核電站,因此建設方就誇大了安全性。比如修建巨大的防波堤就有些自相矛盾。此外對電力公司而言,安全方面的投入也並不是想花多少就能花多少,電力公司受到的制約很多。結果,本應為確保安全本所做的事,實際並沒有執行。
記者:今後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原子能?
益川敏英:恐怕今後也不得不使用原子能發電吧,雖然太陽能等發電方式讓人期待,但由於電力基本上無法儲存,因此很難去依賴這樣的不穩定的可再生能源。另外,由於化石燃料300年後也會枯竭,也不能指望火力發電。
安全性基本上是可以商量的問題。舉例來説,汽車雖然方便,但也有其危險性,每年會有千上萬的人因此而死亡。核電也一樣,我們需要容忍這樣的觀點存在,即正因為核電有這麼多好處,其負面部分也應該接受。其實最恐怖的是核電研究很可能會停止,20~30年間人類可以短時間離開核電,但這一期間核電安全所需要的研究不能停止,我反對終止相關研究。
(記者為日經新聞編輯委員 吉川和輝)
版權聲明:日本經濟新聞社版權所有,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複製,違者必究。
報道評論
HotNews
金融市場
| 日經225指數 | 54253.68 | 435.64 | 02/06 | close |
| 日經亞洲300i | 2632.52 | -18.84 | 02/06 | close |
| 美元/日元 | 157.12 | 0.01 | 02/07 | 05:50 |
| 美元/人民元 | 6.9380 | 0.0009 | 02/06 | 11:20 |
| 道瓊斯指數 | 50115.67 | 1206.95 | 02/06 | close |
| 富時100 | 10369.750 | 60.530 | 02/06 | close |
| 上海綜合 | 4065.5834 | -10.3333 | 02/06 | close |
| 恒生指數 | 26559.95 | -325.29 | 02/06 | close |
| 紐約黃金 | 4951.2 | 89.8 | 02/06 | close |







